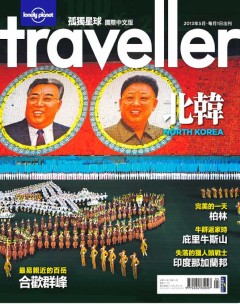|
對那加人而言,割下敵人的腦袋,等於捕獲了敵人的生命力和魂魄。
午後的空氣清新涼爽,聞來有松香的氣味。我把身子探出車窗,聽見某條隱匿在叢林裡的潺潺河水喃喃低語。從竹棚的縫隙望出去,可瞥見谷地和群山,更遠處,則是山裡的鬼魅。群峰相互傾壓,在逐漸黯淡的日光之下,由鮮綠轉為靛青。司機自豪大聲地說:「先生,丘陵到了。這裡就是我們的那加丘陵(Naga Hills)。」
此時,我們已遠離了阿薩姆平原的蒸騰熱氣,依循著蜿蜒的道路向南行駛。沿著150公尺高的岩壁繞行,外側是60公尺深的懸崖,崖下有河,1930年代的茶農指南形容這裡為「漁夫的天堂,駕駛的夢魘」。
此處的視野彷彿無窮盡地開闊,不由得感受到人類的渺小及有限。這裡的杜鵑高度可達30公尺以上,山徑則是幾近垂直地穿入霧中。天氣晴朗時,可望見谷地後方,喜馬拉雅山東側覆雪峰巒矗然屹立,召喚旅人前往。春夏之際,空氣裡瀰漫各種野花的香氣。光是那加蘭邦境內,就有多達360種蘭花,且花名迷人,如仙履蘭、狐尾蘭等,一座座竹林裡的蘭花頓時全數綻放,在綠林裡四處潑灑著紅黃藍的色彩。在更接近緬甸邊界的法金禁獵區(Fakim Sanctuary),老虎依舊在森林裡悠然漫遊。
我站在谷地的頂端, 吃著跟路邊小販買來的鳳梨,憶起了1930年代的英國旅人娥蘇拉.葛拉漢.鮑爾(Ursula Graham Bower)。當時年輕的她來此,自述發現了「一處風景,那魅力是我從其他事物上未曾體驗過的,那股力量超越了軀體,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」。鮑爾來自倫敦上流社會,正值初入社交界的青春年華,就逃離了錦衣玉食的高級牢房,成為人類學者,跟那加人一起工作。在當年,這需要莫大的勇氣,畢竟地方部落當時仍會發起獵人頭突襲。過去商人或許曾打開丘陵區的門戶,企圖進入更廣大的聚落區,可是獵人頭的風俗讓貿易商卻步。
鮑爾對於這種獵人頭文化有自己的諷刺說法:「如果你帶著頭顱回家,就不用擔心對方會繼續追殺你了。」她最後成為對日戰爭首位女性游擊隊長,帶領游擊隊在那加丘陵發動猛烈攻勢,聲名大噪。
我親訪那加丘陵的原因,源自於一場被遺忘的戰役,10年前的冬季午後,1名曾瀕死的軍人向我透露這場戰役的故事。1944年,大日本帝國陸軍入侵印度,在科希馬(Kohima,今日的那加蘭邦首府)這座丘頂市鎮,被迫停下侵略腳步。僅僅1,500名步槍兵的英印駐軍竟擊退了1萬5千人的日軍。陸軍上校約翰.薛普斯特(John Shipster)親眼目睹多名友人葬身科希馬
這可怕的夢魘終其一生糾纏著他。在他年邁之際,拒絕了重返科希馬的邀請:「我覺得自己無法再面對科希馬。」如今,他的兒子麥可就在我身旁。我倆坐在東搖西晃的吉普車後座,打算前往科希馬,這趟旅程是為了紀念約翰.薛普斯特。我這位朋友向來健談,此時卻陷入靜默。我問:「你在想什麼?」他答:「很多事,但主要是在想他。當年他來這裡打仗時才19歲。我不由得想,當時他看到這片風景的時候,心裡究竟在想什麼。打仗的時候,他眼裡的風景還是一樣美麗嗎?」
然而,在這裡人不可能長時間鬱鬱寡歡。一座座小村莊依附於山脊邊緣,我們 每抵達一座村落,就有一大群孩子衝出來揮手歡呼。孩子們高聲齊唱:「哈囉, 哈囉,哈囉。」在距離科希馬16公里處的祖布札(Zubza),一群從稻田返家的婦人停下腳步,加入了孩子們的歡迎行列。
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某名行政官曾把那加人稱作是「自治野蠻部落」,自1826年以來,就不斷有各種政府企圖征服這些山中住民。不過,我們遇到的第一批那加人離「兇殘」二字天差地遠。我們停下來買水果時,那些孩子和周圍 人群都沒有伸手乞討,一次也沒有。司機說:「那加人沒有乞討的習慣。」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