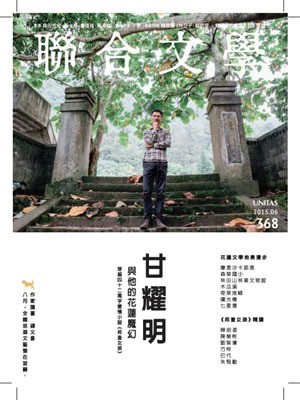|
幾年前,短居在花蓮的時候,我曾經去過幾次林田山。那裡現在是以「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」而為像我這樣的觀光客所知的。整個園區,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有兩處:一是被火災燒毀的屋舍,建築物全毀,但從地上的痕跡,猶能見到當時房間的格局,何處是門窗、何處是浴廁清楚可見,唯所有門牆屋頂都不存在,走在其中,頗有種真幻難辨的奇異感覺。二是一座廢棄的國小——它的操場被改做停車場,每當停好車,前方就是一整排教室,學生奔跑的走廊、高度小巧的洗手台俱在,只是通通堆滿了雜物和居民晾曬的舊衣。教室窗格破碎,有的牆面半坍,有的被裝上了鐵捲門,從外面看進去,好像都住著一小座一小座的叢林,什麼都有可能竄出來。唯有走廊盡頭的廁所,還新簇可用地維持原來的功能。
這是我見過最美的學校。據說,之前本來還留下更大面積的校舍廢墟,這排教室已經是碩果僅存了。
所以,當我讀到《邦查女孩》裡面,古阿霞努力重建的廢棄國小,校舍被挪作豬圈的時候;當我讀到小說末段的森林大火的時候,明知小說的場景和我所看到的很可能有落差,但還是難以自抑地疊合了小說與我的記憶。
而這或者正是像《邦查女孩》這樣的寫實小說,最頑強也最悲傷之處。頑強是說,建物會焚毀、聚落會離散,但只要作品被寫出來,現代的印刷品典藏和數位資料儲存,幾乎能夠保證這些記憶能與人類文明相始終。但也是悲傷,小說是必然的遲來之物,總是在事物已經或快要消亡之刻才會出現。而且無論如何寫實,文字終是無法取代事物本身,頂多作為一種補充的派生物。而當本體完全消亡,只剩下文字的時候,那也就註定只能在讀者心中留下不精確的心象。
往好處想,不精確也就意味著有模糊、曖昧、在創造的空間。甘耀明打造的摩里沙卡,將會是一個純真、溫和、照拂著柔柔笑意的地方。不同於《殺鬼》,在奇詭瑰麗之中有著深重的歷史傷痕,並且具象成為血肉上的折騰(被炸彈炸過的螢火蟲人、把自己種在土地上的老人、拒絕與親族分離而血肉融混的意志力,還有以肉身擔當戰爭機器對抗機器巨獸的咬牙橋段),《邦查女孩》也有歷史、也有傷痕,但卻多能有溫好的結局。尤其在小說前三分之二,每一卷幾乎都是一個兩難衝突,雙方都其情可憫,某種不可化解的情緒對撞在一起,不斷預示著必然的悲傷橋段,然而甘耀明卻總能突出妙手,把球「救」回界內。比如勇犬胖浪咬死了小學生們最尊敬的母豬「朱大媽」,小學生決議吊死胖浪。這本來是個無解之局,雙方都是讀者會認同的正面角色,但甘耀明安排了一隻黑熊出場,給了胖浪表現並且取得原諒的機會。
如是情節不斷出現,不禁讓我想起鍾理和的《笠山農場》。不管是《邦查女孩》還是《笠山農場》,總有一種溫厚的、彷彿來自大地的力量支撐著一切。殘酷的事情會發生,但也都會過去、都能被治癒。這樣毫無火氣的書寫,幾乎是一種人格的展現(尤其考慮到鍾理和的貧病交困,而整篇小說渾然無一絲火星,更覺難得)。我很不喜歡用這種詞彙,但這真的是一種修行、一種境界。
那是一種接近無限的純真。但如果只有純真一色,難免讓小說落於天真、濫情。幸好,甘耀明在結尾的處理,揭露了某些看似巧合的「奇蹟」,背後是怎樣苦心孤詣的運作與算計。純真如同「透明」,唯有另外一種色調墊在底下才能讓我們真切感覺到。在森林與學校、在傳統技藝與工業技術、在利益與純粹的夢想之間,甘耀明想寫的並不是倒向這些拉扯中任何一方的小說,而是人在其中可能的善意與堅強。小說最後刻下的是無可挽回的悲劇、以及可能永遠解不開的誤會。那是甘耀明出給角色、也出給讀者的一組題目:你如何能繼續堅強、善良而溫厚?你如何還能繼續純真?
走過這段長長的小說之旅,我們或者也就能好好在我們生活裡,回答這些問題。
朱宥勳
一九八八年生,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,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國藝會創作補助、全國學生文學獎與台積電青年文學獎。在寫小說、讀小說、學一點理論的同時,也是棒球和電競的觀眾。曾與黃崇凱共同主編《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》。二○一三年起,與一群朋友創辦電子書評雜誌《祕密讀者》。曾出版小說《誤遞》、《噩觀》、《暗影》,文學研究文集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