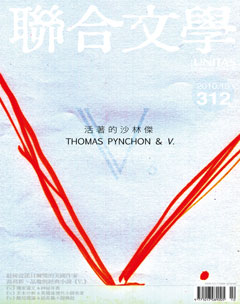|
陳:小說中相當精采的部分,是描寫1935年的台灣博覽會。在建構這段場景之前,你是否讀過日治台灣作家朱點人的小說〈秋信〉。 他的小說也是寫一位漢詩儒者,對日本帶來現代化的政策表達不滿,與你小說中的施寄生可以對照。你的構思是否與朱點人有關,還是不謀而合?
施:斗文先生和我小說中的施寄生應該屬於同類人。如果施寄生參觀博覽會,他和斗文先生一定心有戚戚焉。
1935年的博覽會,日本展現對台灣日本化、現代化的經營成果,殖民者向島上的人民驕示帝國雄厚的實力,也讓全世界看看殖民台灣的成績。博覽會在這部小說中占極重要的分量,我把重點放在新公園(現今二二八公園)的第二展覽館,日本當局用日語教育、神道思想、現代化的科學、醫療知識,來對台灣人進行同化,掃除所謂落後、閉塞的島民信仰習俗,強制改變台灣人的思維及生活方式,與過去歷史切斷,把台灣人塑造成為沒有過去,沒有歷史,只知有大和民族的一群。
日本殖民的終極目標,我以為是想改變台灣人的心靈視野,最後用他們的眼光來看世界,極端的例子就是皇民化運動。
我安排兩個台灣知識菁英去參觀博覽會,一個是被日本人塑造成功的日本化的醫生,一個是反抗,加入文化協會、農民組合社會運動,最後抗爭失敗,不得不屈服,變得頹廢虛無的律師。
醫生一心一意想成為日本人,無話可說。肯定現代化、世界化的律師卻不願意同化於日本民族,他的妻子還是日本人,可是,像他這種不肯屈從殖民者,只認同現代化的知識分子,被日本語言、文化薰習,不斷滲透,也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,動搖了自主性,我想我要表達的是自我與異己之間的混雜所造成的曖昧性。
陳:漢詩人與藝妓的故事,在日治時期的報紙俯拾可見。不過,施寄生與月眉相遇的那段故事,在小說中寫得很傳神,你對月眉有某種程度的同情,但是用力不深。月眉的角色不像過去你的小說受到深刻描述,你的用意何在?
施:我好像特別喜歡描寫身分地位卑微、社會邊緣的女性,「香港三部曲」的黃得雲、《行過洛津》裡的阿婠、珍珠點,演旦角的許情也是吧!我由這幾位娼妓、藝旦、伶人來暗喻被殖民的香港、台灣的處境,一路寫來,到了月眉,覺得夠了。這本書中,這個被大國民從洛津接到台北來唱南管曲給日本人聽的藝旦,隨著時代變遷,聽曲藝的聽眾品味的變化,我描寫她跟隨時尚,放下琵琶,不再唱優雅的南管曲,改學音調高亢的北管,甚至拋頭露臉去演戲。北管、京戲取代了南管,受當時士紳的喜愛,我只是很好奇,聽不懂北京官話的台灣觀眾,是如何欣賞京劇的?還稱它為「正音」。
為了呼應總督的放足政策,也以為脫掉三寸金蓮可以贏得大國民的歡心,她沒想到會表錯了情,原來大國民表面上支持放足運動,骨子裡還是個有小腳癖的傳統自私的男人。不過,月眉後來不願意委身大國民拉線的日本人,不肯賣身給異族殖民者被稱作「蕃仔酒矸」,顯示台灣女人的氣節,我覺得她很可愛。
陳:《三世人》是台灣進入現代化運動以後三個世代的故事。始於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,止於二二八事件的爆發。在整個歷史過程中,台灣人的批判力道似乎顯得衰弱,這是不是暗示你對台灣命運抱持某種悲觀?
施:台灣人是很悲哀的。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,命運掌握不在自己手中,一直都是身不由己,無法自主,真的是一種宿命。
平情而論,草莽強悍、族群意識強、具移民性格的台灣人,歷史上出現過好漢,反清的朱一貴、林爽文,抗日的簡大獅、陳秋菊等,都很轟轟烈烈過。二○年代文化協會、農民組合更是人才輩出,只有到了「二二八」後,才完全噤聲。
台灣人的反抗總是被動,官逼才民反,每一次運動都很短暫,像東部的河流,颱風一來,山洪爆發,溪水暴漲,一下雨過天青,溪底石頭清楚可見,台灣民主國,亞洲第一個共和國,曇花一現,「二二八」事變,九天就結束了,被形容短得像撥一下開關,就把電燈熄滅一樣迅速。
陳儀接收台灣,口口聲聲批評台灣人被日本奴化,這兩個字很不中聽,往深處想,在異族統治下苟活,無形之中形成被殖民者的性格,為了求生存,活得很卑微。
日本領台後,先以同文同種收買人心,接下來強制日語教育,漢文從選修到了滿洲事變後廢止,中日戰爭爆發,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,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,殖民高壓下當二等國民的台灣人,接觸到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、科學知識,走出封建狹隘的儒家思想,把認同有郵電、鐵路、衛生設施的現代化與屈從殖民政策混為一談,從早期的抵抗到晚期的屈服被改造,使台灣人的日本化扭曲曖昧。
※延伸閱讀:
‧和靈魂進行決鬥 (上)
‧和靈魂進行決鬥 (下)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聯合文學》十月號312期;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】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