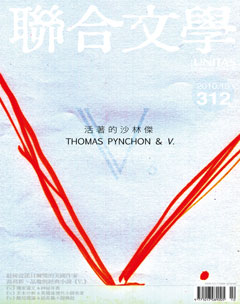|
我在《Cafe Monday》書中寫過這段少年往事。
十幾歲的時候,一個朋友家庭發生嚴重的衝突變故,讓她對於成年人──主要是她的父母吧──產生強烈的幻滅厭惡之感。在那樣的壓力下,她常常或刻意或不經意地喟嘆:「乾脆從十四樓跳下去算了。」
十四樓,那是我們居住區域最高的一棟樓──中山北路上的「嘉新大樓」──的高度。想要跳下去,因為她不能想像有一天自己也會變成大人,變成一個讓她自己厭惡鄙視的大人,可是卻又找不出其他拒絕長大的方法。
那時節,我總是擔心著。我的年紀與情感經驗還不足以讓我分辨,那「乾脆從十四樓跳下去算了」的喟嘆,是一種玩笑、一種發洩、一種憂鬱的反射,還是一種強烈、真切慾望的表達。我能知道、能具體掌握的,只有:她是個我珍視珍惜的人,我甚至無法承擔想像她從十四樓上縱身一躍的影像。
是在這樣的情境下,讀到《夏濟安日記》,如獲至寶。我將密密麻麻畫了線──先考慮到了她會有的感受而特別選擇句行的──的書,捧著交給了她,努力讓自己聲音不顫抖,盡量輕描淡寫地說:「蠻好看的,有空看看吧!」她投給我一個狐疑的眼光,還好,封面上一隻拆信刀刺穿一顆水蜜桃的奇特形象吸引了她,她將書收下了。
在我的記憶中,是《夏濟安日記》救了她,也解除了我日夜的十四樓噩夢。我們討論了《夏濟安日記》,討論了夏濟安這個人,討論了夏濟安到了中年竟然還如此天真地單戀痴戀一位女學生,那感情如此濃烈如此直接卻又如此膽怯如此徒然。
在我的記憶中,《夏濟安日記》說服了我們──當然更重要的是說服她──不是所有的中年人都一樣,我們還有機會將自己活成像夏濟安那樣的中年人,懷抱如此希望,或許長大還是件值得嘗試的事。
我沒有將《夏濟安日記》拿回來,那本《夏濟安日記》後來就隨著她淡出、終至永遠從我生命中離開了。
不記得究竟是什麼樣的場合了,也許是另一篇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,也許是一篇採訪稿,我又提到了《夏濟安日記》,並且提到手上沒有了這本書,且遺憾多次在舊書攤尋訪不遇。
很短的時間內,三本品相不一的《夏濟安日記》送達我手上,來自三位熱心的讀者。那個時代,讀者對於所閱讀到的文字,還有著如此直接、迅捷的反應。
我深深感動。至少有三個人,讀到那文字記述,讀到我的遺憾,起身在自己的書架或書堆前,眼光逡巡流索,找出了那有著拆信刀刺穿水蜜桃影像封面的書,不吝惜更不辭麻煩地將書拎到郵局──那個年代連「快遞」都還不普遍──寄去報社,再由報社轉給我。如此體貼、如此慷慨。
有一本1977年3月的五刷本,不知原讀者是誰,書中全無任何劃線、標記,只在扉頁上以淡色的鉛筆(HB吧!)記了幾行字:「愛你在心口難開,我愛你,不要密而不宣,單相思苦也。愛,神會賜予免於恐懼,我想夏老師士大夫的味道深了一點。建立了幸福美滿家庭有益身心健康,延年益壽。讓我們愛個過(夠?)吧!」
還有一本遠從南投寄來,書中還夾了一紙短簡,用的是「聯合報新聞傳真稿紙」。
楊照兄:
很抱歉,跟你通個電話隔天就來個大颱風,我家小水災事小,南投山區災情慘重,跑了新聞忙了一陣子。
答應你的《夏濟安日記》放在車座,被一堆又一堆的資料壓在最下面,直到前天我才翻出來,一直惦記著要寄出過去,也因此拖了快一個月。……
很驚訝,也很高興,還會有人提及《夏濟安日記》這本書;除了在你的作品中,我覓得了成長的共同記憶外,這本書也讓我感受到「楊照的心情」……
書的原主是當時在南投跑司法、醫藥和產業新聞的記者,叫張家樂。要送我書,先問到號碼打了一通電話,信簡開頭還先道歉,好像反而是他欠了我似的,體貼如是,慷慨如是。
※延伸閱讀:
‧拒絕長大的煩惱──夏志清編的《夏濟安日記》 (下)
|